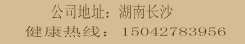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支原体尿路感染 > 中医支原体尿路 > 基于中医药理论的芳香类中药防治新型冠状病
当前位置: 支原体尿路感染 > 中医支原体尿路 > 基于中医药理论的芳香类中药防治新型冠状病

![]() 当前位置: 支原体尿路感染 > 中医支原体尿路 > 基于中医药理论的芳香类中药防治新型冠状病
当前位置: 支原体尿路感染 > 中医支原体尿路 > 基于中医药理论的芳香类中药防治新型冠状病
摘要:芳香类中药自古被用于瘟疫的预防,中医药防治疫病有独特的优势。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肆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指南推荐中西医结合治疗。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的中医治疗方案中,医学观察期、确诊患者的临床治疗期及恢复期均选用含较多芳香类中药的中成药或方剂进行防治,部分地方卫生健康委员会或中医药管理局还推荐多种其他使用芳香类中药的方式(外熏、艾灸、佩戴香囊等)防治COVID-19。芳香类中药“芳香辟秽、扶助正气”的功效在COVID-19的预防和治疗中发挥积极作用,使用芳香类中药干预COVID-19的发生发展已成为共识。芳香类中药独特的药性、化学成分和作用机制值得开展广泛深入的实验及临床研究,可为后续COVID-19治疗及相应的药物开发提供参考。基于中医药理论探讨芳香类中药在防治COVID-19中的作用,并推测其发挥作用的可能机制,为芳香类中药防治COVID-19提供依据。
芳香类中药又称“香药”,能散发出浓郁的芳香气味。芳香类中药自古被用于瘟疫的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属于中医“疫病”范畴,中医药在COVID-19的预防及治疗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芳香类中药多味辛,性温,归经以脾、胃经最多[1],以挥发油为主要有效成分[2]。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芳香类中药具有较强的抗菌、抗病毒、抗炎、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3],内服、外熏、艾灸或者佩戴香囊等方式能够起到早期干预、阻断病程、减轻症状的作用[4-7]。芳香类中药在此次疫情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在COVID-19预防阶段及治疗阶段都有应用,其性温偏燥的药性特点针对此次COVID-19的病机特点发挥了辟秽化浊、健脾除湿、理气化痰、开窍醒神等作用,是一类重要的防治COVID-19的中药。基于此,本文在中医“治未病”思想及“内病外治”治疗原则指导下,探讨芳香类中药在防治COVID-19中的作用,为芳香类中药防治COVID-19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依据。
1芳香类中药应用的历史沿革
我国应用芳香类中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多年前的炎黄时期,其在防治时疫、辟秽解毒、疗疾摄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从西汉以来的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了余次大型瘟疫[8]。在传染病肆虐的过程中,芳香类中药是驱除疫病最常用的一类中药。
殷商时期,人们就发现将芳香气味的中药熏烧或制成香囊挂在身上可以驱虫和预防疾病[9]。汉武帝时期,关中瘟疫流行,人们靠熏烧芳香类中药抑制瘟疫的传播[8]。东汉时期的华佗用丁香、百部等芳香类中药制成香囊预防疾病。《神农本草经》记载药材种,其中芳香类中药约占10%,包括芳香开窍的麝香、菖蒲,芳香化湿的佩兰、厚朴,芳香活血的川芎、当归,芳香理气的木香、陈皮等,都是目前常用的芳香类中药[10]。东晋时期,《范东阳杂病方》中记载采用艾灸预防霍乱[11]。唐宋时期是芳香类中药应用较为成熟的时期。《外台秘要》中记载用艾灸法可防治伤寒、温病及天行、霍乱等传染病[12]。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有大量的芳香类中药和组方,中药有白术、白芷、菖蒲、川芎等,组方有太乙流金散、雄黄丸等,太乙流金散、雄黄丸都是辟瘟气的重要方剂。还记载了多种香疗防疫的方法,其中提到用艾烟熏蒸的方法防治时气瘴疫[13]。《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应用芳香类药物的方剂占35%,如芳香开窍的苏合香丸,芳香理气的木香槟榔丸、沉香丸,芳香活血的乳香散等经典方剂[14]。这一时期,芳香类中药应用十分广泛,在内、外、妇、儿各科涌现出许多方剂,如木香散、五香连翘散、调经散、豆蔻散等。明代《本草纲目》中将植物类的芳香类中药分为芳草类和香木类,其中芳草类有56种,代表药有荆芥、薄荷、香薷、泽兰、苍术、砂仁等;香木类有35种,代表药有乳香、没药、苏合香、冰片、檀香等[15]。其中还记载运用芳香类中药防疫治疫,如在房中可烧苍术、艾叶、丁香等进行“空气消毒”[16]。清代,芳香化湿药如藿香、豆蔻、砂仁等大量运用于临床治疗中,如在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湿病门中,52例病案中有47例运用了芳香类中药,在吴鞠通《温病条辨》中,也运用了大量的芳香类中药,如芳香解表的荆芥、薄荷、香薷、桂枝;芳香清热的金银花、青蒿;芳香除湿的厚朴、苍术、藿香,草果;芳香温里的川椒、丁香、小茴香;芳香行气的木香、白豆蔻、沉香;芳香活血的乳香、没药;芳香开窍的菖蒲、郁金、麝香等40余种[17]。近现代以来,芳香类中药在各领域广泛应用,芳香类中药的科学内涵得到了快速发展的现代技术的深入研究和持续验证。大多数的芳香类中药有效成分得到了阐明,其中的挥发油成分多是小分子物质,脂溶性强,容易被机体吸收。现代药理研究显示中药挥发油在抗炎、抗菌、抗病毒等方面有独特优势,被广泛用于呼吸系统、胃肠道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疾病的治疗[18]。芳香类中药的现代应用方式和范围均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如熏蒸法、热敷法、穴位贴敷与外敷法、足浴与香浴法、嗅香法与滴鼻法等外用方法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对相关疾病显示出了显著的治疗效果[19]。
2芳香类中药的药性及化学成分
2.1芳香类中药的药性
芳香类中药在中药材中占有较大比例,在临证治疗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吕氏春秋通诠》载有“膻、焦、香、腥、朽”五臭之说,芳香类中药的理论与应用可谓源远流长,在《山海经》《博物志》《汉宫香方》《上香方》《杂香膏方》等文献中均有论述[1]。
药性是历代医家在长期医学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用药规律。《汤液本草》所谓:“药之辛、甘、酸、苦、咸,味也;寒、热、温、凉,气也。味则五,气则四,五味之中,每一味各有四气,有使气者,有使味者,有气味俱使者……所用不一也”。中医根据药性用药以调整阴阳平衡,恢复脏腑经络正常生理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目的。辛味是中药药性“五味”之一,也是芳香类中药的重要药性,具有发散、行气、行血等作用。《内经》记载:“辛者横行而散”,经典药性理论有“辛入肺、辛能通气、辛能开腠理”的认识[20]。中药挥发油是辛味中药最主要的化学成分,被认为是中药辛味的主要物质基础。无论其内服还是外用,用药均与药性关联,正如中医强调的“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因此,芳香中药挥发性物质,均应考虑药性特征的影响[21]。温热也是芳香中药的重要药性。如附子、肉桂、干姜等药物得以缓解或消除阴寒证的症状,与其药性温热有关。
郭金龙等[20]从《中药学》年版收录的味药物中筛选出具有芳香之气的79味进行统计,发现芳香药大多为温热药,占75.9%,且多具有辛味,占82.3%,之后依次为苦、甘、酸、涩。芳香药归经以脾、胃经最多,其次为肝、肺经,正如李东垣所说“芳香之气助脾胃”[15]。在认识芳香药的药性特点及治疗机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芳香药性理论,使其成为中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22]。综上所述,芳香类中药多味辛,性温,归经以脾、胃经最多,芳香透散效果突出,临床应用广泛[1]。芳香类中药的主要作用类别及功效见表1。
2.2芳香类中药的化学成分
芳香类中药以挥发油为主要有效成分[2]。芳香性气味成分通常由数十种挥发性成分组成,包括烃类、醇类、醛类、酮类等多类化学成分,常见的代表性挥发性成分有苧烯(1)、芳樟醇(2)、柠檬醛(3)、薄荷酮(4)、百里香酚(5)、薄荷醇(6)、7-反式茴香脑(7)、乙酸香叶酯(8)、肉桂酸(9)等,结构见图1[23]。
中药挥发油多以油滴形态存在于植物表皮的腺毛、油室、油细胞或油管中,或与树脂共存于树脂道内(如松茎),少数以苷的形式存在(如冬绿苷)[24]。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复杂多样,其基本组成为脂肪族、芳香族和萜类化合物等。萜类以单萜、倍半萜为主,通常含量较高,如薄荷油中的薄荷醇可达80%,其具有抗炎镇痛、清凉止痒的作用[25];山苍子油含柠檬醛可达69%,具有平喘、抗过敏、抗菌、抗病毒等作用[26]。小分子芳香族化合物通常具有特异香味和显著生物活性,如桂皮挥发油中含有具解热镇痛作用的桂皮醛[27],百里香中含有止痛和抗炎成分百里香酚[28]。脂肪族化合物包括陈皮中的正壬醇、鱼腥草挥发油中的鱼腥草素等。鱼腥草素有抗菌、抗病毒、增强免疫力的作用[29]。此外,还有其他类别的挥发性成分,如薁类化合物、挥发性生物碱和含硫化合物等[30-31]。
芳香类中药有效成分挥发油多是小分子物质,脂溶性强,容易被机体吸收。现代药理研究显示中药挥发油在抗炎、抗菌、抗病毒等方面有优势,常用于呼吸系统、胃肠道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疾病的治疗[18]。
芳香类中药“取其气而不取其味”,指的是用这种“香气”来发挥治疗作用,这是芳香类中药防病治病的特色。COVID-19患者的主要表现有发热、干咳、乏力等呼吸道症状,少数有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道症状[32]。芳香类中药可解表祛邪、化湿运脾。现代药理及临床研究显示[24]芳香类中药挥发油成分有一定的解热、镇痛、抑菌、抗病毒、镇咳、止喘等作用,还能解除胃肠道痉挛、止呕止泻。提示芳香类中药可以用于改善COVID-19导致的呼吸道及消化道的有关症状。
3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芳香类中药的应用
3.1体现中医“治未病”思想
中医强调“治未病”的思想,即通过中药早期的干预,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强调防患于未然。《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是故圣人不止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金匮要略》中提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这些都体现了中医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思想。中药内服、中药熏蒸、佩戴香囊、艾灸等方法运用芳香类中药发挥防病治病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医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治未病”的思想。
芳香类中药在临床治疗中广泛应用,是一类重要的防病治病的中药。在此次COVID-19疫情中,对于医学观察期患者,如寒湿犯脾,出现乏力伴肠胃不适时,可服用解表化湿、理气和中的藿香正气胶囊;在风热犯卫,出现乏力伴发热时,可服用清热解毒的连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颗粒等,这些方剂含有较多芳香类中药,可在疾病的潜伏期内及早治疗,遏制病情的发展[33]。对确诊患者的临床治疗期选用含较多芳香类中药的清肺排毒汤作为基础方剂,针对患者病程的不同阶段、不同证型,方剂用药有所调整,芳香类中药在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恢复期都有应用[32],这些方剂中所含的芳香类中药发挥了辟秽化浊、健脾除湿、理气化痰、开窍醒神等作用,起到改善患者症状,防止病情恶化的作用[34]。
疫病流行时,古人常利用芳香类中药焚烧进行空气消毒来预防瘟疫,体现了中医“治未病”的思想。《本草纲目》云苍术“能除恶气,古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中药大辞典》记载苍术有显著杀菌效果,常用于空气消毒[35]。在我国传统民间医药学中,艾叶用于预防瘟疫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民间还流行着“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的谚语[36]。熏艾能起到祛邪辟秽、驱虫杀菌的功效。在传染病流行期间,运用芳香类中药进行熏蒸,可以起到空气消毒、预防传染病的作用。
中药香囊用以防病自古有之,佩带香囊是中医“治未病”的又一种特殊疗法。将芳香性中药装入特制布袋中,佩戴在胸前以预防呼吸系统疾病,俗称“香佩疗法”[37]。香囊中常装入藿香、佩兰等芳香类中药,有“通经走络,开窍透骨”的作用,其挥发的气味可通过口鼻黏膜、肌肤毛窍、经络穴位,经气血经脉的循行而遍布全身,起到调节气机、疏通经络的作用,从而使气血流畅、脏腑安和,增强机体抵抗力[38]。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中药香囊的“药香”可刺激鼻黏膜,促进免疫球蛋白的分泌,同时灭杀各种病毒,从而发挥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抗菌、抗病毒等多重功效[9]。
COVID-19发生以来,艾灸被推荐用于预防及治疗疑似病例、轻型及恢复期患者[39]。艾熏起到了空气消毒作用,可以预防瘟疫传播。在临床治疗期,艾灸的应用可以起到抗炎、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防止疾病恶化[36,39]。江医院在隔离病房内对COVID-19患者使用热敏灸疗法,发现患者的症状有明显改善[40]。COVID-19恢复期患者可能遗留肺纤维化,艾灸用于治疗肺纤维化的疗效确切[41]。艾灸不仅能预防COVID-19,还可以作为治疗COVID-19的中医特色治疗手段。芳香类中药小茴香的有效成分对急性肺损伤有较好的防治作用,能改善急性肺损伤引起的发热、咽喉肿痛、咳喘痰鸣等症状[30]。因此,芳香类中药在防治肺部疾病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3.2体现中医“内病外治”的原则
芳香类中药辛香走窜、善循经络而行,中药熏蒸、佩戴香囊及艾灸疗法发挥了芳香类中药解表散邪、理气活血、破瘀散结等功效,芳香类中药的应用体现了中医“内病外治”理论,是临床中医外治法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19]。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体表与内脏由于经络的纵横交错而遍布全身。《灵枢?海论篇》中载:“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清代吴师机提出“凡病多从外入,故医有外治法”“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42]。中医外治法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指一切从体表施治的方法,如针灸、推拿及药物的熏、熨、敷、贴等都属于外治范围。中医“内病外治”与“内病内治”一样都遵循辨证论治原则,外治所用药物虽是体表用药,但仍可通过体表的吸收和向体内的传导发挥与内服药同样的作用[43]。中医“内病外治”是中医治疗疾病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芳香类中药气味芳香,可从皮肤、口眼、鼻等进入人体发挥药物的治疗作用。中药熏蒸、佩戴香囊、艾灸疗法等外治法,都是利用芳香类中药辛香走窜的特性,不仅能发挥芳香辟秽、解表透邪、理气活血等功效,还能促进其他药物的吸收扩散,药效可作用于脏腑,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19]。
在中医“内病外治”理论指导下,芳香类中药在外治法中的应用在此次疫情中显示出了巨大的潜力。《华中科技大学同医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诊疗方案及预防方案》推荐在室内熏蒸中药、佩戴香囊、艾灸等方式以防治COVID-19。熏蒸中药提到可以点燃艾条熏蒸,或选用单味药苍术熏蒸等,医院自制的防感香囊(苍术10g,艾叶10g,石菖蒲10g,薄荷10g,藿香10g),捣碎或研末,1剂为1包,装入致密的布袋中,随身佩戴,或挂于车内,5d更换1次。艾灸选穴为大椎、关元、气海、中脘、足三里等穴位[44]。
4芳香类中药在COVID-19防治中的应用
4.1COVID-19属于中医“疫病”范畴
《素问?刺法论》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吴又可《温疫论》曰:“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有别于六淫外感邪气。此次COVID-19疫情的爆发,传染性强,病情险恶,都是感受外来疫疠之气,病邪主要由口鼻而入肺或直入中焦,属于中医“疫病”范畴[32]。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32],COVID-19患者以发热、干咳、乏力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肌痛和腹泻等症状,重者可出现呼吸窘迫甚至休克。仝小林院士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发现患者多有明显的寒湿之象,认为COVID-19属于“寒湿疫”[45]。此病的病位在肺脾,基本病机特点为“湿、毒、瘀、闭、虚”,根据疾病发展规律,可分医学观察期、临床治疗期(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恢复期3个阶段[46]。
4.2芳香类中药防治COVID-19的临床实践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言:“香者气之正,正气盛则除邪辟秽也”。临床实践中发现,芳香类中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可有效防治COVID-19[39,46]。
由于COVID-19属于“寒湿疫”,为“湿毒之邪”,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中[32],中医治疗方案以祛湿解毒、扶助正气为主。在医学观察期如患者乏力伴胃肠不适推荐服用藿香正气胶囊、乏力伴发热推荐连花清瘟胶囊等,这些中成药成分中含有较多芳香类中药,如藿香正气胶囊中有广藿香、紫苏叶、白芷、白术等,连花清瘟胶囊中有炙麻黄、广藿香、鱼腥草、薄荷脑等(表2)。其中,藿香正气丸中的广藿香以其辛温之性能解在表之风寒,又取其芳香之气能化在里之湿浊,且可辟秽和中而止呕止泻,在方中为君药。
对确诊患者的临床治疗期选用清肺排毒汤作为基础方剂,此方可用于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在危重型患者救治中也可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合理使用。清肺排毒汤源自《伤寒论》古方,由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4个经典方剂调整而成。国医大师薛伯寿指出,清肺排毒汤药性剑指寒湿之邪,能有效防止患者轻症转为重症。基础方中21味中药,其中10味中药是芳香类中药,如芳香解表、发散风寒的麻黄、桂枝、生姜、细辛;发散风热的柴胡;芳香燥湿、健脾益中的白术;芳香理气、燥湿化痰的陈皮、枳实、款冬花;芳香化湿、解毒辟秽的藿香。
芳香类中药在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恢复期都有应用,针对患者病程的不同阶段、不同的证型,用药有所调整(表3)。轻型寒湿郁肺证推荐处方中有羌活、贯众、藿香、佩兰、苍术等;湿热蕴肺证推荐处方中有草果、厚朴、柴胡等。普通型湿毒郁肺证推荐处方有生麻黄、茅苍术、广藿香、青蒿草等;寒湿阻肺证推荐处方全方除槟榔外,均为芳香类中药;重型疫毒闭肺证推荐化湿败毒方,基础方中芳香类中药有生麻黄、藿香、厚朴等。危重型内闭外脱证推荐送服具有芳香开窍、行气止痛的苏合香丸,此方集诸芳香类药物于一方;还有清热解毒、开窍醒神的安宫牛黄丸,方中冰片、郁金芳香辟秽、化浊通窍,麝香开窍醒神、雄黄辟秽解毒。恢复期肺脾气虚证推荐处方中芳香类中药有陈皮、炒白术、藿香、砂仁。
部分地方卫健委或中医药管理局也积极发挥芳香性中药抗疫的作用,使用熏蒸或佩戴香囊、香包防治COVID-19。这些方式提高了中医药介入的参与度,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任伟钰等[47]对全国各省区中医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疗方案用药规律分析,早期用药出现频次较高的前10味中药中化湿药有4个(厚朴、藿香、草果、苍术),这与国家诊疗方案治疗原则辟秽化浊、健运脾胃相对应。化湿药中大多为芳香之品,且味辛,性温偏燥,临证多适用于阴寒病证,能够祛除寒湿之疫,正对此次COVID-19的病机特点。
在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转载请注明:http://www.niaoluganrana.com/zlzy/4715.html